来源:书城杂志
原标题:伍尔夫的鼻子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1882-1941)
文 | 林晓筱
根据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平和作品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上映之后,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和编剧迈克尔·坎宁安(也是原著同名小说作者)受到了各界的批评。国际伍尔夫研究学会的副主席甚至感觉受到了冒犯,直呼“我必须捍卫我的领土”。评论界的不满集中在女影星妮可·基德曼扮演的伍尔夫上,确切说,矛头就对准了影片中“伍尔夫”的那只鼻子。平日里因学术观点争得面红耳赤的专家们,这一次站到了一起,怒不可遏地说:“昔日高贵典雅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现在却变成了鼻子丑得不行的残障傻瓜。”此言一出,《纽约时报》评论家帕特里夏·柯恩立马写了一篇名为“鼻子,最后的稻草”的文章,将影片中伍尔夫的鼻子当成是压死这位女作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柯恩和伍尔夫研究界所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柯恩所说的“稻草”(鼻子)其实压死的是这部电影,它给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带来了抹不去的瑕疵。而让诸多学者和伍尔夫爱好者感到厌恶的原因是,这只鼻子毁了伍尔夫本人。
电影上映之前,伍尔夫研究界就对大众对伍尔夫的偏见耿耿于怀,这位现代主义作家的偏执、疯癫凝结成了固有印象,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甚至就连她的创作也成了病态催生的产物,这类观点更在女性主义者的眼中,成了男性对“女性写作者”冰冷的凝视。评论界和伍尔夫的拥趸致力于还原真实的伍尔夫的形象,却等来了这样一部雪上加霜的电影,其愤怒也就不难理解了。针对这只鼻子,伍尔夫的传记作者赫米奥尼·李在其随笔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鼻子》(Virginia Woolf’s Nose,2005)中有过专门的论述,但受限于传记文学这一主题,赫米奥尼未能具体展开有关这只鼻子的信息。因此,针对伍尔夫这只鼻子的真实情况,以及它存在的内在意义,值得在此加以评述。
鼻子的主人
伍尔夫研究专家玛莎·马斯格罗夫教授在看过影片《时时刻刻》之后,对演员妮可·基德曼的鼻子产生了“退避三舍”之感。她认为:“妮可·基德曼在整部影片中总皱着眉头,双眼朝中间聚拢,显然对长在脸中央的那个东西感到不满。难道当代关注伍尔夫的人只对她的鼻子情有独钟吗?对于我来说,我从未将伍尔夫的长鼻子当作她的外貌的决定性特征。”
一九○二年,乔治·贝雷斯福德拍摄过一张二十岁时的伍尔夫的照片,她那时的容颜足以打动所有人。照片中的面容处在惺忪的灵泊状态,仿佛沉浸在梦境之中。梦状的清晰,留下的是美感的波纹。后来,另一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这样形容她的长相:“纯洁而忧郁,深陷的双眼怯懦而惊恐,长着一只挺拔如鸟喙的鼻子,双唇却紧闭不开。”伍尔夫的面容不遮瑕,也不提亮,召唤出的更多是距离感。从这张面容所拉开的距离观之,单论这只鼻子,未免有破坏整体的煞风景之感。从她留下的任何照片中,人们实难看出这只鼻子有什么特别异样之处,更别说有“退避三舍”的感受了。那只引发争议的鼻子,肯定不是伍尔夫的。

二十岁的伍尔夫,乔治·贝雷斯福德拍摄
反观基德曼,在《时时刻刻》这部电影中,她的鼻子确实显得尤为突兀,它超越了五官的平面,像一个高台之上的审查官,负责审核其他五官传递出的情感。在影片的多数桥段中,基德曼饰演的伍尔夫,神情紧张,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可言。难怪伍尔夫的爱好者和研究专家会把矛头对准演员。不过,这种指责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基德曼本人的鼻子并非这个样子。据她说,呈现在影片中的这只鼻子是假的,它和假发、服装一样,是扮演伍尔夫的一个道具,每次拍摄前要花三个小时安装这个“道具”。在她看来,这只义鼻“是次要的层面,首要的层面是内在的气质”。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对这只鼻子也有自己的苦衷,他在面对外界的质疑时说,剧组只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来拍摄妮可·基德曼的戏份。要想塑造伍尔夫这一角色,时间是关键。导演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演员和角色糅合在一起。相比衣装,面容是直接向观众呈现的部分,而在五官当中,只有鼻子是立体的,它最容易“捏”,也是天然的目光聚焦点,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选择鼻子作为最快体现角色的塑造部位。

妮可·基德曼在电影《时时刻刻》中饰演的伍尔夫
基德曼所说的“气质”,就像这只鼻子一样,其实是一个“捏造”出来的中间状态:既是伍尔夫的,也是基德曼的。问题就在于,导演和演员选择了五官当中最立体的器官,却演绎了一个最平面的角色。其平面感在于缺少叙事。
鼻子的叙事
影片遭到质疑之后,戴德利针对伍尔夫研究界所说的“领土被侵犯”一说,气愤地回应道:“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宣称这是他们的领土。”这一番孩子吵架般的回复除了让人感到好笑之外,也让人感到困惑,他的意思究竟是指,他所建造的这块鼻子的“领土”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还是想说这片“领土”是一片公共区域,谁都可以进入?模棱两可的态度背后,戴德利忽视了关键的因素:这片领地的领主、这只鼻子的真正主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围绕着这只鼻子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一九三四年某日,伍尔夫去逛商店时,忘了带钱包,选购的商品已经包装好,一时间让她陷入了尴尬境地。情急之下,她突然想到了父辈留给她的这只鼻子,于是凭借这只鼻子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被允许赊了三英镑十便士的货款。这只鼻子在伍尔夫的家人眼中是一只“学者之鼻,尽管长得很大,但长得匀称,鼻尖锐利”。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娘家——斯蒂芬家族——向来以出作家和学者闻名,在身份社会尚留有余温的时代里,鼻子连接着身份地位,象征着信誉和威严,能靠它赊账自不足为奇。有趣的是,伍尔夫在与外界交流,尤其是陷入窘境的时候,这只鼻子除了“最后一根稻草”之外竟也会成为“救命稻草”,这说明伍尔夫本人对自己的外貌,怀揣着转变为“交换资本”的期待。当然,“资本”来自家族的遗传,对于伍尔夫的鼻子来说,重要的是她想以此“交换”什么。“交换”当然也不仅仅局限在鼻子上,它关系到作家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怎样的世界。这是有关“鼻子”的叙事内涵。
拉尔夫·帕特里奇在《伍尔夫的肖像》(Virginia Woolf Icon,2000)中指出,伍尔夫从不搽化妆品,日常穿着有大划口的睡衣,上面罩着晨衣,脚上趿着室内拖鞋。当她出现在印刷间时,会用敏捷的手指排版或拆版,全然一副“不修边幅的天使”的形象。机器、睡衣和敏捷的手指,三者隐喻距离较远,犹如超现实主义诗歌中极富诗意的意象,勾勒出一套融合了生产和生活却不带异化感的和谐图景。整洁属于维多利亚时期“家庭天使”的保洁范围,她们重复着家庭的一尘不染,其洁净包含着孩子的微笑、丈夫的惬意,这张由体面和静默所撑起的家庭保鲜膜,受力最多的地方也是最稀薄的,全靠韧性来维持。整洁就是一种韧性,是布尔乔亚一成不变的生活粘连。伍尔夫不自觉地游走在传统的边缘,如果传统的戏份必然是整洁的,那么她的“不修边幅”也是一种现代性视野下,“新之美学”(语出贡巴尼翁)的典型范例。
不过,伍尔夫并非狄金森那样深居不出的人物,随着小说《雅各的房间》出版,她迅速成了一位名人,出席各类社交场合的机会突然变多了。友人建议伍尔夫出席社交场合要“穿戴整齐”,她对这一要求感到紧张。“穿戴整齐”比“整洁”更多一层要求,它不仅要求室内的体面,更需要遵从室外的姿态与礼仪,当她不得不去面对这些尘埃与喧嚣的时候,寻求权衡的方法也就由此萌生。其中一种方式便是折中,比如组建布鲁姆斯伯里小团体。参与其中的人或是她早已熟悉的,或是新进慕名而来,伍尔夫作为东道主显得游刃有余。这群人虽以剑桥为基,但散发出的活力却比剑桥人士更为生动。亲历过布鲁姆斯伯里社交活动的奈杰尔·尼科尔森曾精辟地认为,布鲁姆斯伯里和剑桥的区别在于:“在剑桥没有人会说俏皮话,除非它包含深远的意义,而在布鲁姆斯伯里没有人会说深沉的话,除非它也很有趣。”(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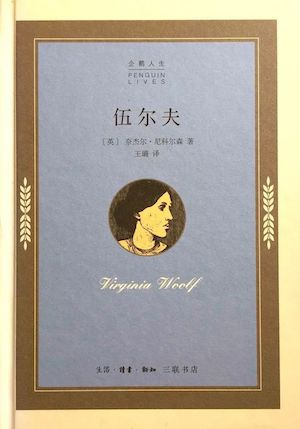
《伍尔夫》
[英] 奈杰尔·尼科尔森著 王璐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版
深沉与有趣,构成了一股特有的张力,对于伍尔夫而言,就如同印刷机和睡衣一样,形成了反讽和悖谬,她在其中自如地穿梭。唯一对此感到不安的,反倒是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在日记中谈论她的社交活动时,曾这样写道:“伦纳德对我在鼻子上搽粉,把钱花在衣服上缺乏好感。不过没关系,我崇拜伦纳德。”当然,伍尔夫所说的“崇拜”并不意味着屈从,更多的是看到了伦纳德身上与她相似的隐秘特质。伦纳德自幼罹患手抖的疾病,伍尔夫认为这种疾病“错误地塑造了他的人生”,但是,没有这种痼疾,伦纳德在社交中“体现出的羞涩与痛苦,他所表现的尖锐和坚定,一定不会如此强烈”。伍尔夫并不会因在“鼻子上搽粉”受到丈夫的指责而难过,她所能接受且包容的社交生活必然包含这种反讽意味,伍尔夫不仅安然处在这种模式之中,也善于对外展现这种反讽,这构成了她与外界的较为重要的处事方式之一。
比如,一九一○年二月的那场著名闹剧。伍尔夫打扮成阿比西尼亚的门达克斯王子——“包着头巾,身穿绣花束腰长袍,腰间悬着一条纯金链。她的脸是黑的,惹人注目地留着非常美观的八字须和一嘴胡髯”。其目的是戏耍英国海军,享受一趟免费且有向导的舰船之旅。在随后根据这一事件改编的小说《社交圈》里,伍尔夫借此表达她对男性的荣誉、暴力和愚蠢的认识(昆汀·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 全二卷 )
[英] 昆汀·贝尔著 萧易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无论在熟悉的环境中,还是置身于陌生的场合下,面容是伍尔夫的反讽和修辞,伍尔夫依靠修辞而叙事,这是她作为一位现代作家书写自己、书写生活,更书写生活中的自己的方式。反讽意味着表达和内涵的脱节,伍尔夫的“不修边幅”镶嵌在“天使”的语境中,凸显着这类脱节,但“不修边幅”没能否定“天使”,“天使”也未能盖过“不修边幅”,在两者留出的裂隙中,伍尔夫得以阐释自己。当这种阐释流露在那场闹剧中时,伍尔夫又敏感地捕捉到了其文学表达的内涵,通过化装,凸显出了讽刺他人的意味。阐释是面容上纷然落下的词语,如同玻璃上的雨滴,当人们注意雨滴下落的痕迹时,模糊的是整片窗户。无法抹去的是雨滴落下的瞬间。伍尔夫的生命和写作的内核在于“存在的瞬间”(moment of being),在这一维度中,痕迹未来得及充分地展现,却早已融入整体的朦胧之中,这是典型的现代时刻,德彪西的音乐,莫奈的绘画,也当作如是观。一言以蔽之,伍尔夫的面容,不是迎合他人的粉饰,而是一场集合了阐释和叙事的印象。
作为符号的鼻子
不过,印象是模糊的,电影里的伍尔夫必须清晰,哪怕是片面的清晰。
作为一部结合了伍尔夫作品和生平的改编作品,《时时刻刻》的确需要冒险。这种冒险超出了凝视女性、曲解作家、冒犯权威“领地”的范畴,具体落实在观众是否能够准确捕捉到其内涵上。电影中有关伍尔夫的刻画,其实只是伍尔夫的一面,若当成对伍尔夫全方位的解读,未免显得鲁莽。就如同这只鼻子一样,导演未能顾及的是伍尔夫芜杂的生活全貌,刻画的是伍尔夫围绕《达洛维夫人》所展开的一次创造,这也构成了这部电影对《达洛维夫人》的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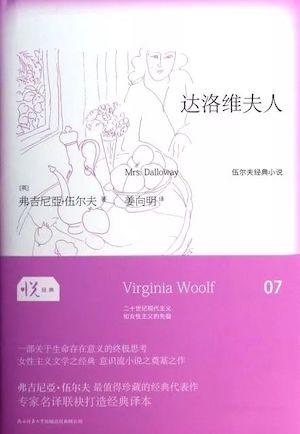
《达洛维夫人》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姜向明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达洛维夫人》的其中一个创建在于将两个平行的人物拧成一股冥冥之中相连的细线,并将这股细线惊心动魄地穿过生与死的针眼。其惊心动魄不仅在于穿越生之日常、死之盛宴,也在于将两个人物串联在一起的方式。影片《时时刻刻》也是如此,它将三段故事揉捏在一起,借助电影的叙事逻辑,展现出特有的关联,留给观众有关女性、生命、家庭、爱等元素的整体印象,影片穿越三个时间,亦在突出《达洛维夫人》主题的经典性。只不过,这里的“整体印象”是蒙太奇逻辑中产生的拼贴效果,它需要以最典型的一面来对接最深远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导演让演员带上的假鼻子才具有了刻画的意义。说到底,导演不是在展现伍尔夫的故事,而是抽取其符号特性,这种符号特性就落在了那只鼻子上。
这里所指的符号性,根据的是皮尔斯所言的“符号三分法”,遵循的是“一物替一物”的逻辑,强调“类象符号”(icon)和“引得符号”(index)之间的关系。“类象符号”睹物思人,通常意义上的人物肖像就是这类符号,以肖像和真人之间的“相似”性(比如按图索骥)为底色。而引得符号,有引,有索,有得,注重的是事物间的“比邻”关系(如看到沙滩便觉得有大海)。这两类符号,显然程度不同,但包含了同样的隐喻指称逻辑,其中指称和被指称物之间的远近,决定了符号嬉戏程度的深浅。由此观之,《时时刻刻》中刻画出的伍尔夫的鼻子,其实构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符号网络。
由于该片导演截取的是伍尔夫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亦即片面的伍尔夫,所以他拍摄出来的效果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错误索引。比如,影片中呈现的伍尔夫是在写完《达洛维夫人》之后立即投湖自尽的,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伍尔夫研究界对此怒不可遏,惊呼:“天啊,他(指导演)竟然要杀死伍尔夫两次!”再者,伍尔夫投湖自尽的场景被导演刻画得过于诗意,让观众不免于恍惚之中辨识出奥菲利亚的影子,这其实与伍尔夫实际自溺的场景相差甚远。“鼻子”的问题亦是如此,由于它撇除了伍尔夫自身的叙事,突出的其实是一只“嗤之以鼻”的鼻子。在妮可·基德曼的鼻子上垫高的那一层,突出的是伍尔夫不近人情的一面。继而,这一层由高耸的鼻子“索引”到的、象征着“势利”的符号,迅速蔓延在影片中伍尔夫的整个脸部表情之中,构成了一副“肖像”符号,将伍尔夫定格成了一个专注于内心世界,对外界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许敌意的人。参考皮尔斯的符号学,可将此过程戏谑地表述为:伍尔夫的肖像是柴,鼻子是火石,点燃的是文化贵族的势力之烟。
当然,在这一发明并传播符号的过程中,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并非始作俑者,他和《时时刻刻》的作者一样,都是传播伍尔夫片面印象的参与者。伍尔夫的“刻薄”“专横”并非个案,也是诸多现代主义者身上的共同特征,它与现代主义者所处的时代和阶级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主义者面对大众必定是有姿态的。如果观众不得不接受影片中伍尔夫那只高耸的假鼻子,那么也应该看到这只鼻子亦是对大众的反叛。这里所说的大众,更准确地说就是二十世纪初的布尔乔亚,他们是市侩、庸众的代名词。与血统论上的贵族不同,现代主义者身上所谓的“精神贵族”“文化精英”,除了后人贴上的文化“刻奇”标签之外,其内涵在于求新。现代主义者与任何一个带有“先锋”意味的时代开创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没有“向后看”的维度:相较于文艺复兴向古希腊、罗马文化回溯,浪漫主义者含情脉脉地投望中世纪,现代主义者的求新,不在于“重新”,而在于“创新”。在这个语境中,过去若不能成为现代主体自身的历史,从而如同艾略特、乔伊斯等人所构建的与传统的隐秘联系,那么这一切都必将是掩耳盗铃式的重蹈覆辙。现代主义者割裂过去,关注当下,但这个“当下”不包含现实主义描摹出的大众的庸俗残余,而是一种人为赋予的艺术秩序,雷蒙德·威廉斯将这一现象解读为:“布尔乔亚是敌对的,或是冷漠的,抑或仅仅是庸俗的大众,创造性的艺术家要么决然忽视避开他们,要么必须日益震撼、嘲弄和攻击他们。”(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1989)也只有在割裂“当前”大众维度的“当下”语境之中,赋予过去的“新”才具有真正超越古典意义上等级判定的能力,迈向精神加速的未来。由《达洛维夫人》所衍生出来的《时时刻刻》,在抓住其人物关系的融合(影片中以三个吻作为剪辑点,凸显了导演的才华)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一次一旦加速便停不下来的风暴,它必然会盘踞在现代性维度下的个体身上。遗憾的是,导演遮蔽了这只“高耸的鼻子”带来的创新内涵,在这一场自我虚设的符号游戏中,自投罗网,也难怪会被伍尔夫研究专家当成网中的捕获物,肆意批评。导演显然不愿就此坐以待毙,他所给出的反对“领地”的做法,其实是在捍卫一种跨媒介的阐释权。
鼻子的阐释
伍尔夫的鼻子能不能阐释?
作为后来者,阐释伍尔夫的鼻子,也就意味着在书写这个人,那么上述问题也可以这样问:究竟怎样才算是在书写伍尔夫?
对此问题,赫米奥尼·李认为关键在于厘清“make up”和“make over”这两个词。她指出,根据《牛津英语字典》:“‘make up’指的是(部分)构成或组成一个整体;从部分或者要素中整合或调配好某物(比如泥浆);在纸上编排文字或图像;杜撰或者发明一则故事。而‘make over’则有两个意思:将一个人的所有物转交给另一个人;完全转变或者重塑某物。”
作为书写伍尔夫的体裁,传记在赫米奥尼看来就成了:“从各种部分(事实、见证、流言和年表)中创造出一个整体来,并将它编排在纸上,又因为传记作家经常挪用他们的主题,并试图创建全新的、特殊的传主形象(比如理查德·艾尔曼版的乔伊斯),并赋予这些材料以一种半小说式的,类似故事的架构(要不就没人读得懂这些了),基于此‘make up’和‘make over’这两个词都是合适的。但从相反的意义上来说,这两个词包含着改编和不真实的一些形式,只对‘相似性’负责,并具有准确性的要求。”
换言之,在赫米奥尼看来,传记者就游走在“make up”和“make over”之间,一极连着相似性,另一极连着准确性。但奇怪的是,赫米奥尼没有提到“make up”一词较为通俗的用法:化妆。对于伍尔夫的鼻子来说,这是最直接的体现。围绕着这只鼻子所展开的一系列的言说,其实或多或少地都在给它涂抹上化妆品。而“make over”这个词,更多强调的是“创造”,是一次“整容”,《时时刻刻》这部电影对伍尔夫鼻子的“加工”属于这个维度,其本身超过了普通传记的范围。

电影《时时刻刻》海报
值得指出的是,伍尔夫不仅热衷于读传记,也擅长撰写传记,甚至影影绰绰地在小说中构建自己。从她撰写的诸多散文中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传记”“回忆录”等体裁展开的,其中以《花岗岩与彩虹》这部文集最具代表性。在题解“花岗岩”与“彩虹”内涵的重要文章《新派传记》中,伍尔夫勾勒出了传记发展的脉络。在她看来,传记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十八世纪是“生硬、结实”的花岗岩阶段,注重材料的堆积;十九世纪的传记中,强调传主人格、心理等方面的“彩虹”特性逐渐增强;而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传记篇幅的逐渐减小,传记作者却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其中,借写他人,言说自己。换言之,传记经历了从“make up”到“make over”的发展。尽管伍尔夫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们也很难说得出那些传记作家能否十分精细地、十分大胆地表现出那些梦境与现实的奇怪融合,那花岗岩与彩虹永恒的姻缘。”但是,伍尔夫自己确确实实具有联姻这两者的能力。在一篇名为《站在门边的人》的文章中,伍尔夫用最短的篇幅为读者勾勒出了诗人柯勒律治的形象。这个“站在门边的人”是她通过信件解读出来的核心意象,柯勒律治为何会吸食鸦片?又为何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却词不达意?这一系列由印象、传闻所构成的疑问,伍尔夫通过分析诗人生活中的仪态、写作中破折号较多的英语表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柯勒律治的生活和写作中,信件和鸦片具有一样的功能,借助烟雾和连缀的词语,伍尔夫看到的是柯勒律治唱响的一曲“塞壬之歌”,它迷住了众人,也借助逃遁了自己,使得他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站在门边的人。伍尔夫其实无意间拓宽了传记的表达领域,似乎在她这里,“make up”和“make over”有了全新的结合方式,材料本身通过传记作者而发出了连传主自己都无法听到的声音,真实的虚构、虚构的真实,得以真正地融合,她或许并不清楚,传记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成了评传。
伍尔夫的鼻子是家族留下的素材,利用这只鼻子,无论是拿来议价还是化妆,
都构成了个人经历的叙事,至于被垫高的鼻子,则属于阐释,这些组成了一个符号体系,浓缩了一个人的方方面面,若将这些有机融合在一起,就成了有关这个复杂个体的传记。
电影《时时刻刻》中只有一幕略微闪过了“评传”的影子。基德曼所扮演的伍尔夫来到了树下,安葬一只小鸟。在镜头中,基德曼的鼻子和小鸟冰冷的喙贴近,形成一组有关生死的类比阐释。借助这个类比,这只义鼻超越了单一的符号性,填补或者延续了叙事。只不过,这个镜头一闪而过,割断了本可以继续展开的可能,显得突兀,继而成了伍尔夫研究专家口中“过度阐释”的典型。或许,当鼻子超过了自身言说的能力,过于明显地留下人工斧凿,它就走向了瓦解。瓦解之后,鼻子连同伍尔夫本人,成了一系列碎片,伴随着这些碎片,现代主义者伍尔夫的姿态,进入了电影院,重新进入了布尔乔亚的风雅之中。
有人认为,碎片就是所谓后现代的表征。
(本文原刊于《书城》2020年2月号)


